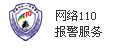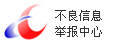克服抑郁:从康复者到同伴 |
 |
“一个个体只有在他的时代才能理解自己的经历并掌握自己的命运,只有意识到他所处环境中所有个体的生活机会,他才能理解自己的生活机会。”王惠喜欢引用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的名言。他是抑郁症的伴侣,也是抑郁症的恢复期患者。通过陪伴计划,王辉开始了解这个时代的共同困境。
陪伴计划是中国抑郁症互助社区“杜杜”自2018年起推出的治疗康复项目。它通过让患者和家属提供陪伴服务,理解患者对病情的感知,为患者提供支持,创造更有利于其康复的生活环境,帮助患者和家属少走弯路,用他们的经验和教训帮助患者和家属少走弯路。
陪伴
停不下来的“过山车”
王辉是同伴,说明他也是精神病人。
2014年大三,王辉变得拖拉。她不想每天起床上课,也不想做老师布置的实验作业。出国交换生的手续很难办。异国情调下,他没有朋友,不会说语言,开始变得比较暴躁。
这种烦躁体现在他的两个极端。这一周,他可能情绪低落,只想赖在床上,连去吃饭的兴趣都没有。下周,他可能会翻身下床,到处乱跑,去酒吧购物,用信用卡疯狂购物。王辉用“过山车”来形容自己的状态。一开始中间有几天平稳过渡,后来干脆一天一天变得一样。
班主任推荐他去找心理老师,心理老师判断他是躁郁症,让他去医院仔细检查。
“你有病,要吃一辈子药。”在北京安定医院,医生的诊断让王辉很反感,他心想:“我没病。”
没有治疗,王辉的状况依然不好。学校老师从安全角度出发,让他先回家休息。回到家,看到焦急的父母,王辉更加痛苦。他觉得很愧疚,觉得自己在社会上站不住脚,会连累父母。虽然他的父母试图和他说话,但他一个字也不想听。最后住院治疗也只是略有好转。
毕业后疾病一直困扰着王辉。他只有条件好的时候才能工作,只能兼职帮人编辑一些文章和稿件。在编稿的过程中,王辉学到了很多小说以外的东西。“我发现一个作品其实一拿出来就不是成品,可以不断修改。比如那个作者,他写得很好,但是错别字很多。”王辉意识到,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自己也没必要去追求。
在此期间,王辉加入了一个关爱抑郁症患者的公益组织,结识了“穿越”抑郁症互助康复社区的张进先生。
过来人的陪伴、“连接”和“退出”
2018年6月,张晋启动了陪伴计划,这是他患上抑郁症后的第7个年头。在张晋患病的过程中,他出身于媒体,将自己的患病经历发表在一篇稿件中。很多病人和家属陆续来找他。他们发现精神疾病在交流方面非常复杂,而且没有标准-like过程进行治疗。结合自己在治疗中走的很多弯路,张进觉得如果有人过来指点一下自己就太好了。
随着病情的好转,张进开始反思自己从患病到治疗的经历。他发现现有的治疗系统不够完善。目前我国精神疾病的治疗主要由医疗卫生系统和心理咨询系统三三五四组成,即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咨询师,但他们都有各自的局限性。共同的缺点是他们不能给病人提供全职帮助。
于是,伴侣计划诞生了。张进希望精神病康复者能以“陪伴者”的身份出现在患者身边,与精神科医生、心理咨询师一起,形成三位一体的治疗方法,突破“生物(医疗)-心理(辅导)-社会(陪伴)”三个环节,全程给予患者指导、陪伴和安慰。
张进看过王辉的情况,觉得可以做“同伴”。每一个“同伴”都是经过专业人员考核的,有的同伴会在“穿越”的社区做一段时间管理员,考核合格后才能转正。
2018年至今,王辉作为“同伴”陪伴了近百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是青少年,其中一些人,王力可回族,是躁郁症患者。
陪伴的方式有很多,线下交流,电话或视频,微信。
文字聊天的。王辉发现,求助者有很多都是家长,他们最常问的问题是:“我孩子得了抑郁症,怎么办?”作为曾经的抑郁症患者,王辉现在可以很理解这些患者家长,他告诉家长们,孩子选择不见你、不跟你说话,并不是他讨厌或者恨你,其实他也很难受,很内疚,他们会觉得“我作为儿女让父母承受了这么多痛苦,我不配活着”,所以他们才把自己关起来。
作为陪伴者,王辉的一个任务就是为患者和家长建立更多的连接,然后再慢慢退出来。因为陪伴者很难一辈子陪在患者身边,但父母却能够这样做。“我觉得,父母是最好的陪伴。”
王辉曾经接到过一个来自江西的求助者,对方是一名边缘型人格的男生,平时有经常性的自伤行为,一旦有情绪问题处理不好,就会用刀子割伤自己。对于这位求助者,王辉陪着他聊天,陪他一起打游戏,那些二次元的东西,王辉也一知半解。虽然王辉自己觉得,这种聊天颇有些“尬聊”,并没有多么亲近,但从那个男生的反应来看,有人陪着他玩游戏聊天,有人能够听他讲讲自己的经历故事,就已经很满足了。
在这个过程中,王辉也帮助男生与他的妈妈建立起更多的联系,他会跟男生说,有些问题你可以去问问你爸爸妈妈,他们能够帮你解决。通过这种引导,男生与妈妈的关系开始亲近起来,经过王辉半年多的陪伴,男生都没有再出现自伤行为。
理解
陪伴者的真正困扰,是失落
“陪伴者计划”的任务原则是案主自决,这一点类似于社工,且不是纯粹的公益活动,陪伴者是按照时间来向求助者收费的,收费的价格很低,即便是等级最高的陪伴者,一个小时也只需要200元。
对此,张进解释,收费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求助者来说,付费的才会珍惜,才不会随意消遣陪伴者。另一方面陪伴者花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去帮助求助者,理应获得报酬,虽然报酬不高,但这对陪伴者来说是一种认可,同时由于陪伴者多是心理疾病康复者,他们也需要社会认同,获得报酬能够更好地帮助他们回归社会。
事实上,陪伴者或多或少都能够从“陪伴者计划”中获得心灵上的收获。王辉发现,不断讲述自己的经历,并没有因此而影响自己的情绪。他觉得有人能够听他讲自己的故事,能够感受到自己的生命被别人重视,对别人有帮助,这其实对自己是一种疗愈。
当然,由于陪伴者本身就是抑郁症康复者,不断地提及自己患病的过往,也会导致个别陪伴者出现情绪反复的问题。按照项目要求,如果陪伴者发现自己在陪伴过程中情绪受到了较大的影响,或者是回溯自己过往经历后有不适状况,就要立刻停止陪伴,由专业心理咨询师介入。
同时,为了防止类似事情发生,陪伴者管理团队会定期安排心理督导,一方面帮助陪伴者提高陪伴能力,另一方面也让陪伴者认清自我。
对于大部分陪伴者来说,真正困扰他们的倒并不是自己的状态出现反复,而是无法给求助者提供帮助时的失落感。
王辉在陪伴中就发现,并不是每个求助者都能够有明确的求助方向,也不是每个求助者都能在陪伴者的帮助下摆脱引发困扰的环境和事件。
有一次一个女生陷入抑郁在网上直播自己喝得烂醉如泥的样子。后来王辉约她到北京陪伴她。王辉能够感受到,这个女生与男朋友之间的关系对她是个伤害,但无论他怎么做,那个女生都无法完全放弃这段关系,总是会回到关系里去继续痛苦。王辉发现对待这样的事情,自己其实什么都做不了。
起初,王辉深深地陷入到无法帮助到求助者的自责中,但接到的案例越多,他开始慢慢释怀,他明白有些事情是不能替求助者解决的。但无论怎样,能够在一个人需要的时候给予陪伴,也对他们有足够的帮助。
陪伴
宽容的环境
理解的空间与支持的力量
这种失落感,其他陪伴者也有。刘昕也是“陪伴者计划”中的一员,在他陪伴的过程中,有一个案例印象最为深刻。求助者是他的发小,他有很明显的抑郁症状,刘昕建议他去看医生,诊断是双相情感障碍,医生建议他治疗,但他的妈妈始终觉得孩子没有病。去年七月时,这个男生自杀身亡。
这件事让刘昕很遗憾,他觉得自己当初没有做好,应该更坚决地让他妈妈带他去住院治疗,如果那样很大可能会救下朋友一命。
“我们的陪伴就是帮助患者增加社会连接,让他们学会如何去生活。”刘昕说,陪伴者并不是老师,并不能教给求助者如何去生活,但可以给他们创造一个宽容的环境,一个理解的空间,一个支持的力量,让他们自己去摸索,想明白如何去生活。“当然,有的人很快就能够摆脱自己的状态,有的人则需要很长时间,几年都有可能,我最长的一个陪伴有两年时间。”
在陪伴的过程中,陪伴者偶尔会遇到求助者有寻短见的情况。根据陪伴者管理规定:遇到这种情况,需要突破保密协议,第一时间通知紧急联系人,并且向家人推荐专业医院或者机构进行救治或者危机干预。
“陪伴者计划”对于陪伴者的任务有明确守则,除了心理危机问题外,在用药上也必须严格遵守,陪伴者可以和求助者讨论药物的使用,但不能建议求助者用药或者换药,并且一定要叮嘱求助者用药前必须咨询专业医师,在医师的指导下用药。
刘昕现在就是精神科专业的研究生,他也同样不会轻易给求助者建议用药,即便对用药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他也要让求助者去征求专业医生意见。
学习精神科专业后,刘昕对于“陪伴者计划”可以从专业方面进行评价,他认为陪伴者对于病患来说是有直接帮助的。在国外对待精神疾病的患者时,往往会由一个医生配合几个风格和流派不同的治疗师,其中还有社工的深度参与,这一整个团队为一个精神疾病患者提供生物、心理和社会的三维治疗康复服务。其中社工的工作与陪伴者非常接近。
只不过,“陪伴者计划”来源于“渡过”这个抑郁症患者互助社群团体,他与精神科医生和心理治疗师是割裂的,三者无法像国外那样信息共享,这还有待中国精神卫生治疗康复方面的进一步完善。
支持
共享教训,一位母亲的转变
对于这些年龄小的孩子,陪伴者与家长的交流更为重要。刘昕认为,孩子出现心理问题,家庭环境肯定是无法规避的环节。有一些父母觉得孩子有精神问题,于是找陪伴者来陪伴,还有一些家长因为孩子患病也焦虑烦恼甚至抑郁,他们也需要调整和改变,只有整个环境都调整,对于患者才有最好的效果。
腊梅是一名陪伴者,同时她也是一名抑郁症患者的母亲,在“陪伴者计划中”她接到的求助者也同样以患者家长为主。看到那些家长的状况,腊梅有时会想起自己,她儿子在患病期间,她也曾备受煎熬,也曾深陷焦虑。
现在,腊梅会把自己带儿子看病的经历,当做一种教训讲给求助家长听,让他们不要犯同样的错误,便于尽快找到帮助孩子并让自己走出焦虑的出口。
腊梅的儿子曾是重庆重点中学的好学生,模拟考试能考到600多分,目标就是清华北大这样的高等学府。但从高二开始,他就出现各种症状,上课就头疼,晚上就失眠。精神科医生诊断他是严重焦虑,但只开了一些中成药。药吃了还不到一周,儿子就开始抵触治疗,不再吃药,可是症状仍然困扰着他。
腊梅和丈夫带着儿子四处求医,有的医生说孩子没病,有的医生说是双相障碍,有的医生说是抑郁症。每个医生有每个医生的治疗方案,开了很多不同的药,这更让腊梅焦虑,儿子到底是怎么了?在这兜兜转转中,孩子也陷入到一种很崩溃的状态,有的药物导致他嗜睡,他在课堂上睡着了,醒来更觉得自己有负罪感,还有的药物对他没有作用,反而加重了症状,他甚至还出现了自杀的倾向。
在四处问诊的过程中,腊梅的儿子仍旧坚持复习为高考做准备,参加了各种复读班。2017年、2018年和2019年他三次准备高考,但临到了考试时症状就会越发严重,结果反而一次都没考成。在这期间,孩子也一直尝试自救,但都没什么效果。
直到2019年,腊梅带着儿子到北京回龙观医院就诊,医生经过两个小时的问诊,建议他不要再强迫自己考试复习,顺其自然,直到这个时候全家才下定决心放弃高考。
现在腊梅儿子的情况比较复杂,自我效能感很低,觉得自己有病什么都干不了。他曾说:“妈妈,我以后真的不能工作了,我干什么都不行,也不能结婚了,我就能凑合活着就不错了。”儿子现在这个状况,腊梅也没办法。
腊梅成为陪伴者后,会参加社群的心理专业培训和陪伴者督导,她会和专家聊起儿子的情况。现在她反过头来认为,自己当初带着儿子四处投医问药的做法欠妥,使用各种药物后,反而把他的病情搞复杂了。
腊梅现在也对青少年抑郁有了自己的思考,她认为青少年的心理问题比成年人的更复杂,她回想起儿子患病的经历,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当时她和丈夫对精神疾病完全不懂,认为治好了症状就什么都好了。所以,丈夫还一直让儿子坚持复习,期盼他治好后能参加高考。“但其实,孩子的病根就在考试的压力上。”
康复
疗愈彼此,找到陪伴的意义
面对求助者时,腊梅会先询问患病孩子的情况,然后告诉家长:“这时你不能焦虑,必须站起来,去了解抑郁症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应该怎么治疗康复。”
腊梅会告诉妈妈们,孩子出现抑郁情况后,除了要积极就医外,还需要家长全面梳理家庭关系和生活环境,要了解孩子的性格以及父母及亲子之间的关系等,这些都梳理清楚后,再结合学到的心理学知识,来分析孩子所处的环境到底是哪出了问题,然后一点一点去解决。
腊梅想起自己的家庭关系,丈夫是老师,平时略显清高,不善与人沟通,对儿子的学业寄予厚望。她自己曾经比较强势,努力工作赚钱,追求完美、追求成功,追求金钱。而此前她有时会抱怨丈夫,丈夫则以冷暴力来回应她,而丈夫会用责打的方式管教儿子,这个时候作为妈妈的她又从来不出来劝阻。
“你问我有没有自责过,当然有,我觉得每个抑郁症孩子的父母在重新审视过家庭环境后都会有自责。他们会问自己,我这么爱我的孩子,但怎么却成了这样的爸爸妈妈?”腊梅说,但如果真的能够懂得心理知识,这种自责就会慢慢消失,父母们也就会释然了。“我的问题是我的父母的投射,那我父母的问题呢?如此往下推导的话,我们到底应该去责怪谁?以前我不懂,我会恨我的父母,现在我懂了,我可以释怀了。”
腊梅说,以前孩子没生病时,她表面看起来生活很好,其实心里却焦虑得很。现在,腊梅打算去考社工师,来帮助更多的家庭解决问题。“最近这两年我跟丈夫的关系也在好转,我们夫妻关系得到了疗愈,我陪伴的求助者很多人也都在调整自己的家庭关系和状态,有时候想想,这是我儿子给我们带来的改变,这其实就是他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他用他的痛苦、经验和教训,帮助了我们。”
在陪伴的过程中,腊梅觉得自己也收获了很多。去年她陪伴的一个求助者,是一位母亲,因为孩子的病,这个妈妈也抑郁了,曾经多次想自杀。腊梅跟她通过话后,两人在线下见了面,腊梅陪她聊了三个多小时,后来还一直保持着联系。通过腊梅的陪伴,这个妈妈调整了心态,慢慢地状态好了起来,没多久,孩子也停药了。她给腊梅发信息说:“我必须要发自内心地感激你,是你帮我掀开了盖在头上的盖子。”
在后来的交流中,这个妈妈和腊梅互相学习探讨,腊梅也觉得受益匪浅。
通过“陪伴者计划”腊梅认为心理健康知识对于预防青少年心理问题非常重要,她希望学校可以将心理健康知识纳入到日常教学中,让孩子们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而对于已经患有精神疾病的孩子来说,她认为根本无法靠父母来解决,必须要借助外界的力量,这所谓的外界应该包括精神科医生、心理咨询师和治疗师以及类似陪伴者这样的社工。“当年如果我们家有一个像我现在这样的陪伴者,能够帮助我们引导我们了解抑郁症这个病,我们也不会走那么多弯路。”文/本报记者 张子渊
医药网新闻
- 相关报道
-
- 你有起床气吗?4个妙招,教你缓解暴躁 (2025-06-17)
- 阳光明媚却“情绪流感”高发 春天“惹的祸”? (2025-04-01)
- 12356!“没事儿”热线如何解“心事”? (2025-01-07)
- “12356”热线来了!如何判断焦虑抑郁情绪是否成为病态? (2024-12-26)
- 临近开学如何做好心理准备?专家来为家长和孩子支招 (2024-08-28)
- 专家呼吁构建职场人群心理健康支持体系 (2024-07-19)
- 浙江多方合力 共话青少年心理健康“最优解” (2024-06-25)
- 五部门启动困境儿童心理健康关爱服务主题活动 (2024-05-30)
- 算命app排行榜前五名 算命app哪个好用? (2024-03-22)
- 谨防节后焦虑加疲劳 专家建议关注心理健康 (2024-02-05)
- 视频新闻
-
- 图片新闻
-
医药网免责声明:
- 本公司对医药网上刊登之所有信息不声明或保证其内容之正确性或可靠性;您于此接受并承认信赖任何信息所生之风险应自行承担。本公司,有权但无此义务,改善或更正所刊登信息任何部分之错误或疏失。
-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医药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本网转载其他媒体之稿件,意在为公众提供免费服务。如稿件版权单位或个人不想在本网发布,可与本网联系,本网视情况可立即将其撤除。联系QQ:896150040